<股票配资网大全>大数法则:保险业数理基础,风险与损失的必然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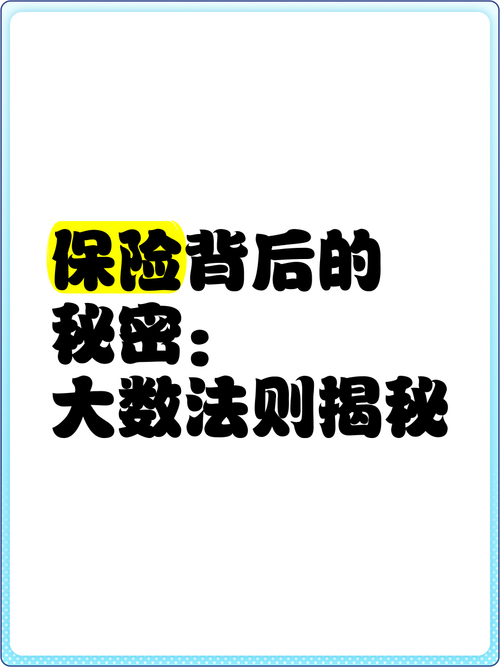
大数法则大数法则又称“大数定律”或“平均法则”。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在随机现象的大量重复中往往出现几乎必然的规律,即大数法则。此法则的意义是:风险单位数量愈多,实际损失的结果会愈接近从无限单位数量得出的预期损失可能的结果。据此,保险人就可以比较精确的预测危险,合理的厘定保险费率,使在保险期限内收取的保险费和损失赔偿及其它费用开支相平衡。大数法则是近代保险业赖以建立的数理基础。基本简介 又称“大数定律”或“平均法则”。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在随机现象的大量重复中往往出现几乎必然的规律,即大数法则。此法则的意义是:风险单位数量愈多,实际损失的结果会愈接近从无限单位数量得出的预期损失可能的结果。据此,保险人就可以比较精确的预测危险,合理的厘定保险费率,使在保险期限内收取的保险费和损失赔偿及其它费用开支相平衡。主要作用 大数法则是近代保险业赖以建立的数理基础。保险公司正是利用在个别情形下存在的不确定性将在大数中消失的这种规则性,来分析承保标的发生损失的相对稳定性。按照大数法则,保险公司承保的每类标的数目必须足够大,否则,缺少一定的数量基础,就不能产生所需要的数量规律。但是,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有它的局限性,即承保的具有同一风险性质的单位是有限的,这就需要通过再保险来扩大风险单位及风险分散面。如何形成 大数法则何以形成,我们以排队为例。我们在超市购物,形成队伍的因素往往是偶然的,但只要是加入该队伍的人数达到一定数量,个别人如果要形成另外的队伍,那么就会遭到多数人的抵制。其原因是“无论指示人们排队行为讯号是什么,一旦建立的队伍,就会从这个现存的队伍本身导出一套排队的规则,或者透过那些发挥非正式的’管理者职能’的排队者的指示,而使其他人获悉此一规则。”并且,有一些人会基于自身利益的维护而自动充当起了维持大数队伍秩序的角色,并且这种角色仅仅因为人数较多就轻易地获得了正当性和有效性。而那些想插队或者想另辟蹊径的人基于多数人的心理压力往往只能选择跟从,并且随着跟从的人数越来越多,队伍的稳定性也就越来越强。当然,如果破坏队伍的人数达到一定数量并成为一种多数人的行为时,原本的多数法则就不再是大数法则了,或者说一种新的大数法则替代了原来的大数法则。 再以交通规则形成为例,人们在行车时都有约定:或者都靠道路的左侧行驶,或者都沿沿右边行进。虽然,这种约定现在看来是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的,但这样的法律无非是给予早已存在的社会规范以正式地位而已。这种规范最初是如何形成的呢?比如,沿着一条过道向相反方向行走的许多人会趋向于自行组织起来,形成两股方向相反的人流,由是为了避开相撞而迂回地行动。这种分行通道的形成是自动出现的,但哪条通道向什么方向通行却纯属偶然。而一旦形成,想通行的人则只能加入既定的人流中。在各国道路交通规则的例子中,有两种可能的习俗:向左驶和向右驶。他们在每个人看来都是同样的好。英国司机靠左行驶而不是靠右,这是任意的历史事件,和不公平无关。只要能保证足够的人数遵从,那么,少数人就只能按照多数人选择的方向行驶,否则就违反了大数法则而被制度所否定。在交通行动中,向左行还是向右行原本和道德无关,但一旦形成为某一方向的大数法则,那么,和大数法则相反的行动就构成了不道德的行为,道德的评价和人数的多寡在这里发生了勾连。因此,一个人的行为之所以不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行为者在人数上的少,而不是源于其在动机上的恶。 从上述例子,我们发现,大数法则的形成和人们之间的相互模仿的社会关系有关。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必然要和他人发生关系。“社会关系’这个概念的基本特征,就在于行动者和他人间存在着最低限度的相互关联。”这种相互关联是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信任是社会交往的前提,是社会内聚的粘合剂,否则人类生活和动物生活无异,因此,信任和合作对于人类物种的延续具有进化的作用。信任和合作的天性首先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普遍存在着互惠关系和信任关系,这是一个无需证明的先定的生物性事实。但是,当陌生人成功地摹仿了我们的亲人或朋友的行为时,我们就将这种信任和互惠关系延及到了陌生人。于是,和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也由是开始大数法则:保险业数理基础,风险与损失的必然规律?,社会关系得以展开,人类社会得以形成并延续。人类得之于上帝的模仿天性催生了人类行为彼此的相似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模仿是人类文化主要的传播方式。模仿意味着服从对方或表达尊敬之意,目的是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并希望被对方接纳,以融入对方的群体之中。所谓入乡随俗、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从而形成了群体成员行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为个体之间彼此的行为提供了可资预测的根据。这种模仿不只是发生于小孩对大人世界的行为规则的模仿,也经常发生在个体和群体的关系上。模仿是一种简便易行且非常实用的交际方式。如果其他人已经全体一致采取了共同的决定,那么,个体可能会忽略自己的观点,别人怎么做就跟着怎么做。这并不是说跟着别人做的人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而是因为别人的行为毕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可以参考的信息来源。别人怎么说就怎么做总是比自己劳心费神琢磨出来的办法简便得多,有用得多。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对于未来的预测,经验总比理性在人们的心理上感觉更为可靠。此外,部分原因也还因为如果大家有错,也是有很多人的错,个人因继续犯错而受到的社会压力和道德压力也因为人数的众多而趋于减弱。并且有时,如果违背群体意识认可的规则还需要具备很大的勇气。当然模仿也可能发生在个体和权威者的关系上,当权威者的行为被大数人所模仿时,群体行为的大数法则便已形成。而一旦形成群体行为的大数法则,个体屈于群体意识的压力,自觉不自觉地选择遵从,甚至是盲从。因为在群体中,具备强大的个性足以抵制那种集体意识暗示的个人几乎没有。因此,在强大的群体意识的支配下,自觉的个性往往消失。这也就可以解释,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陈规陋俗,比如农村习俗中的婚礼,虽然从理性上判断并无太多的道理,但仅仅因为是群体意识所强烈支持的大数法则,那么后代就会自觉和不自觉地模仿和沿袭,因而也就具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在群体意识的支配下,人类模仿的天性有效地保证了大数法则的历史延续性。 人类生活是一个集体生活,任何人都无可逃避。生活是不能选择自己的世界的,它从一开始就只能在一个既定的、无法改变的世界中发现自己。在集体生活中,对集体生活的有效形式进行选择和决定,根源于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大众人。对团体生活有害的东西往往作为禁忌规则来要求个体予以抵制,因而大多数人的生活习性和生活规则对集体生活中的个体构成了压倒性的影响。因此,人的意识反映出来的往往首先是团体意识而不是个体意识。在这样的群体社会里,人类的整体性往往作为神秘的力量而为人们所意识并为人们所坚持,这是不需要更多理性考虑的。整体意识对个人行为的要求是不需要理由的,它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个体意识的要求甚至是压迫,个体意识只能寻求和整体意识的一致才可以被团体所接受。对制度经济学颇有研究的康芒斯认为,大家所共有的原则或多或少是个体行动受集体行动的控制,因此,制度可以解释为集体行动对个人行动的一种控制。习俗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强制,是那些同样感觉和同样行动的人的集体意见对个人的强制。多数人坚持的制度和习俗就是大数法则的载体。 现代社会是典型的陌生人社会。在陌生人社会里,陌生人之间如何能发生信任和合作的关系取决于陌生人是否会根据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中归纳出来的大数法则而行动。换言之,人们是根据大数法则来对陌生人的可能行为作出预测的。大数法则可以使人们生活得简单而有序,它在人际关系中提供了成本最小化的约束机制。为了确保合作的不成为不道德的侵略者的“猎物”,霍布斯主义者认为,在一个共同体中道德行为必须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规范,以致每个人都能期待:如果他合作地行动,其他人也会同样行动,反之亦然。这些约定(习俗)组成了一个社会的道德制度。当这种约定为多数人所遵循时,就构成了多数法则的内容。商业法律的产生就是源于商人们基于彼此交易的需要而自发形成的,而对于那些不守老规矩、违反条例规定的商人惟一和最终的惩治措施就是所有的商人都不再和其进行任何交易,因而,商人之间的规则在多数商人的有效执行下得以延续并完善。当然,人们之所以采纳某些规则,是因为每个人都会从别人按照某些规则行事中那里得到好处。这也是商业法律能够得到普遍遵守而成为大数法则的原因之一。大数法则作为法律基础法律规则,至少从起源上看,不是靠推理而产生,而是来自人类社会经验的大数法则。法律最早来自习俗。习俗和习惯紧密联系,当一个习惯被一个部落或一个社区大多数人所遵从后,就形成为大数法则,并极易被一代代沿袭下来,从而对叛逆者的个体构成极强的约束力。并且人数越多,其约束力也就越强。这种约束原本是心理上的,后来才演变为物理上的,并最终上升为法律。如果说,某个法律的确具有公众认可的道德基础,这也是依赖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多数人成功地垄断了甚至是强行灌输了他们的支配符号。法律必须吸收大数法则的内容,其区别只在于法律是常规化、制度化的大数法则。帕森斯认为,当自我的服从和其他人的服从趋于一致,成为获取他人支持性反应和避免他人不利性反应的条件。如果,和很多行动者的行动相关联,对某一价值取向标准的服从满足了这一尺度,那么,这个标准就可以说是被制度化了。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在行动中的模仿和被模仿,结果是规则的形成,而制度化的规则便是法律规则。法律规则和大数法则的先后关系好比货币的发明,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大数法则是对的吗,金银作为交换的媒介并不是因为先有了法令才产生了这样的发明,而很有可能是因为参和以金银作为媒介交换的人越来越多,最后那些少数人发现如果要和他人合作必须接受原本他并不喜欢的金银。人类进入国家时代以来,法律为国家立法所垄断,法律出自国家成为法律规则产生的主要方式,但这并没有切断法律规则和大数法则的联系。法律规则源于大数法则,或者说许多法律规则本身就是出于对大数法则定律的维护。法律就是人类大数法则之一,并且是重要的大数法则,是通过国家强制力而保护的大数法则。大数法则之所以被吸收成为法律规则首先是因为大数法则的实用性,这种实用性表现在人数上的多数从而导致规则的自动有效,强行执法的成本被节约,尤其重要的是,社会秩序呈现出井然有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当法律规则进入到国家法时代或者说立法时代以来,即使是国家立法成为法的注要渊源,大数法则对于法律规则的渊源作用也不能否认。法律规则对普遍人性的尊重便反映了大数定律对法律规则的要求。只不过,法律规则的立法更强调技术罢了。法律规则之不同于大数法则就在于法律中的大数必须精确,而大数法则中的大数往往比较模楜。法律必须对大数法则进行分级制以保证精确,比如人的成年和未成年的划分,多数人心智成熟标志的平均年龄就是其重要的依据,而一旦进入法律规则,就还必须将这一年龄精确到一个具体的时刻。法律规则中关于推定的抑制其实就是建立在大数原理的基础上,即建立在人们日常生活经验或行为所呈现出来的总体趋势和规律的基础上,否则推定就很难成立。这表明,人类社会进入法律立法时代以来,法律规则所反映出来的大数法则更多的带有技术上的痕迹,这是人类规则的进化,而不是大数法则的消失。当然,说法律规则渊源于大数法则,这是就人类行为规范化的历史进程而言,并不是说一项具体的法律规则都必须以先在的大数法则为前提。事实上,进入国家立法时代以来,许多法律,特别是技术性的法律,如交通规则中信号灯的设置及其象征的意义,这些其实就是由交通法进行原初创设的。国际金融中的银行结算、市场交易中的合约担保等,法律规则也完全可以在无先在的情形下得便宜设立。这种现象并不表明大数法则的失效,当这项原创性的法律规则强制实施一段时间后最终被大多数人所依从,立法创始的规则就表明已经成功地转化为一项大数法则,或者说国家通过立法也可以创设大数法则。但是,如果立法的创造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多数人的行为标准,只是依赖强制,那么该项规则要么被指责为暴政,要么是实效性极低,最终摆脱不了“法之不法”的命运。因为,当观念通过不同的方式,深入到共同体的头脑之中并且产生了一系列的效果,比如说已经形成作为共同体的大数法则时,和它对抗就是徒劳的。美国禁酒令的失败就一个有名的例子,美国当前在毒品、赌博和卖淫方面还依然重复着这种失败。=因此,法律规则的生命力仍然是以大数法则的支持为根据的。这就提醒我们,法律规则在立法时必须考虑大数法则,即必须尊重“常人”行为的本性并以之作为法律行为的标准。这就要求立法时必须警惕“少数人的偏见”,防止在一起的少数派的利益被过度代表的现象。在国家立法时代,也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多数法学家对法律的研究都不是从数据和经验出发,而是根据道德伦理的假定前提予以展开。他们会先做出人们应当如何行为的若干假定,然后在此基础上构筑其理论模型,接下来便是根据模型提出对不符合其理论模型的人的行为进行如何干预的建议。其结果是精英们通过所谓的理性裁剪了生活,其制定的法律背离了公众的真实生活,这种现象反过来却被法学精英们指责为公众对法律的背离。不仅是立法,还有司法,也不能不尊重大数法则的定律。诉讼中证据的认定以及所运用的司法推理就充分考虑了大数法则的原理。法律对诉讼中盖然性证据的肯定其实反映的就是大数法则的定律要求。因为,依赖证据还原事实真相的想法已经被证明不切实际,因而,证据的证明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说服力。证明力的大小并不是靠理性作支持的,而是以经验为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中多次重复出现的频率或普遍呈现的现象其实正是司法认知的依据,并且也是较为可靠的认知保证。正如经验主义者皮尔士所宣称的“只要人们对于某一思想、概念有坚定的信念,只要它们不再有怀疑,不管它们是否符合实际,都可以宣布是可靠的真理。”意思是说,大家共同持有的经验就是生活的真实内容。法官在作出判断时必然会受到其日常生活经验的影响,只不过,法官个体的经验不能代替公众的经验。正是为了防止法官以个体的经验代替公众经验的倾向,各国广泛采纳了陪审团制度。陪审团制度背后的理论基础在于陪审团成员和被告人在人格上具有的同构性,这种人格孤同构性是建立在陪审团成员和被告人有更多共同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陪审团成员的直觉和经验的判断因为和被告有相同或相类似,因而也就更能赢得被告人的充分依赖。因此,陪审团制度有效地化解了法官过度专业化和过度精英化的思维倾向,从而有效地“保证了他们(被告)的权利不受法院专制作风的打击。什么是犯罪?表面上看,犯罪是因为触犯了法律。但法律为什么将此种行为,而不是将彼种行为确定为犯罪呢?按照涂尔干的说法,“犯罪乃是每个社会成员共同遣责的行为。”社会成员之所以共同遣责这一行为,乃是“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和共同意识。”而对于这种强烈而又明确的集体意识的违反,其行为就是犯罪。因此,“我们不应该说一种行为是犯罪的才会触犯集体意识,而应该说正因为它触犯了集体意识才是犯罪的。我们不能因为它是犯罪的就去遣责它,而是因为我们遣责了它,它才是犯罪的。”刑法的主导地位必须以这样的条件为前提:具有一种非常清晰的集体意识,存在为社会成员所共同拥有的信仰和情感。惩罚首先是对违法行为的一种情感反应。法律是来自持续性的规范经验。犯罪是对一般的存在状态的偏离。犯罪总是意味着少数人的行为和多数人的行为发生了偏差。但是,在许霆案的判决中,尤其是一审判决,无疑指向的却是多数人的行为和少数精英认可的规则,或者说是常人的行为和圣人的行为发生了偏离。而这种判决的指向无异于对社会成员普遍赞同的情感行为发生了严重的偏离。既然犯罪是偏离了社会成员普遍赞同的情感,那么,对犯罪行为予以矫正以使其回归到共同意识的轨道就成为,并且也一直是支持刑事惩罚存在的主要依据。因此,矫正的是行为者的主观恶意,而不是行为者的结果,即行为的社会损失并不是矫正的出发点。根据大数法则原理,法律规定中关于人的善恶程度的判定总是和多数人或平均人所反映出来的人性特征联系在一起。因此,法律对主观恶意的评价更多的是基于统计概率,而不只是基于道德上的直觉。打个比方,我们许多人宁愿借钱给一个从未见过的外国银行,也不会借给一个急需钱的陌生人。尽管道德上鼓励我们帮助这个陷于绝境的陌生人,但法律仍然不能惩罚他,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信任陌生人而宁愿相信一个未曾谋面的机构。但是,有亲缘关系就不同了,法律往往要求亲缘关系的人有相互帮助的义务,那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信任并愿意帮助和自己亲近的人,于是,法律牵就大数而作出了迎合的姿态。可以预测。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是按大数法则行事,那么,即使是道德不鼓励的行为,也会被人们从普遍人性的角度去予以理解甚至是给予宽容。对通奸和嫖娼不作刑事犯罪处理,“食、色,性也”便是其直接的原因,而所谓的“性也”无非就是普通人或多数人的本性反映。刑法对犯意的分级就更直接反映了统计学上的概率要求。美国刑法中关于一级谋杀和二级谋杀的区别,虽然法律上有情节轻重之别,而情节的轻重又何尚不是犯罪人数多少的反映。法律对于过失的评价也是如此,什么是“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其依据其实就是将“平均人”或“常人”的行为本性作为法律格式化的标准。因此,法律责任轻重的背后“应该”也“必须”和大数定律保持内在的相关性。许霆的贪心是普通人常有本性的反映,对于这种普遍人性弱点的矫正,应该施以何种力量或者施以多大力量是必须和其人性联系在一起。刑法始终坚持维护所有人之间相似性的最低限度。犯罪的性质和频率是呈反比关系的,越是比较罕见的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惩罚就越重。而对于许霆所反映出来的这种普遍人性的弱点,刑法是否必须,或者必须至何种程度对这一人性弱点施以强制的矫正,就需要人们冷静地予以反思。公众对于许霆的一审判决,表现出强烈的对抗情绪,这是因为判决已经破坏了人们心目中的大数法则,并强烈冲击了人们对维持秩序的法律体系的信任。须知,“在每一个法律体系里,一个规范被正式适用的首要功能不在于惩罚某人,或者回复正义的状态,或者通过惩罚或折磨违法者以彰显正义之神的作为,或者血债血偿,当然这是在流血被认为是必要的情形下。适用法律最为急迫的目的还在于维持该系统的可信度。”因此,为了维持公众对法律的可信度,法律的惩罚仅仅是意味着法律尊重并保护公众对大数法则依赖的心理,并根据公众的这一心理依赖而维护一种可以有效预测的社会秩序。要求官职业的保守性就是要求法官尊重并维持公众依赖的既有社会秩序的连续性,而不是创造一种新的生活秩序。一个最不可欲的社会不是实在的法律规范被违反,而是公众普遍信赖并强烈依赖的社会机制突然无法有效地运作而陷于瓦解。当法官的判断改变了公众基于人性的普遍期待时,也就意味着司法判决割裂了真实生活的连续性,从而导致公众陷于不安恐惧的状态之中。公众对于许霆案的判决所表现出来的激烈情绪其实就反映了原有判断标准的突然失去,而滋生的



